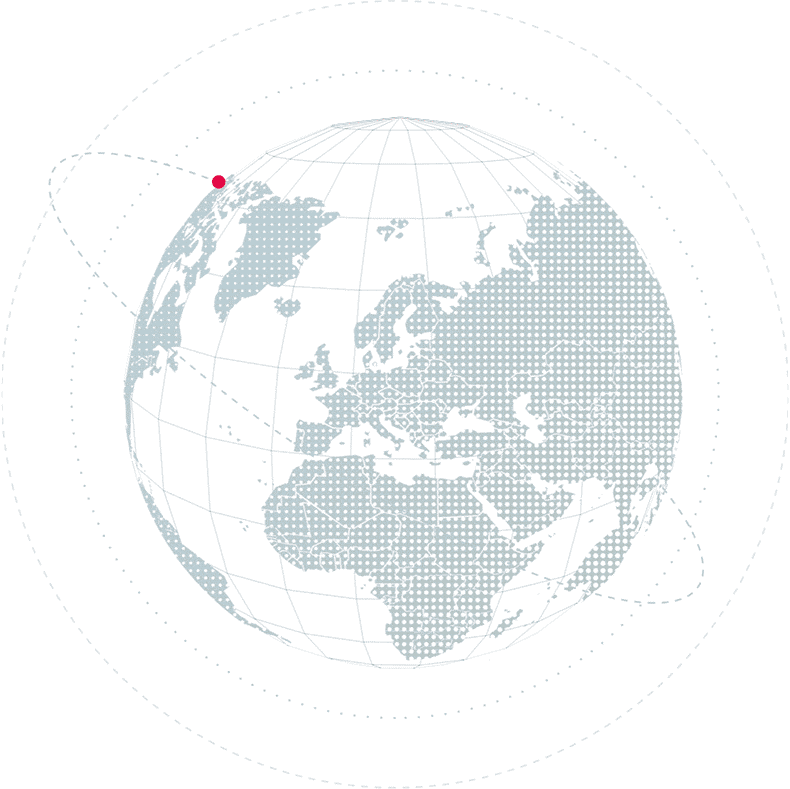黃來興: 另一種汽車夢

《杭州日報》記者 齊航
坐在記者面前的黃來興侃侃而談,講到興奮處雙眼會笑得瞇成一條線。你會驚嘆于他的記憶力,通過他的回憶和描述,一幅微縮版的市場化改革圖景躍然于眼前,那是他的奮斗史,也是一家脫胎于社隊企業的集團公司的成長史。
你甚至會忘了這位亞太機電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亞太機電)的掌舵者,已經70歲了。他依然會在每天早晨7點多,就出現在公司辦公室里,幾十年如一日。他將一家掙扎求存的社隊企業帶出虧損泥潭,通過技術和產品創新,逐步發展成為國內自主研發整套汽車制動系統的領軍企業,并率先登陸資本市場。
從實現汽車制動器國產化的等效替代,到率先攻克“汽車防抱死制動系統”(ABS)自主研發難關,到推動汽車系統集成的電子化、智能化升級,再到前瞻布局新能源汽車輪轂電機領域,黃來興說亞太機電會一直專注于為整車配套服務的主業,也會根據行業趨勢和市場需求應時而變。
黃來興用他的創業故事,詮釋著另一種汽車夢。
一盆冷水 澆不滅創業斗志
黃來興說他是伴隨著一種“饑餓感”長大的。缺糧食,缺物資,缺學習的機會,彌漫在當時鄉村社會之中,也彌漫在這個蕭山農村娃長大的年歲里。彼時的黃來興并沒有想到,他的人生會與汽車制動器如此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初中畢業后,黃來興上過一年半的財貿干校,在社隊林場做過會計,之后進入杭州市蕭山石巖公社農機廠工作,這是一個在計劃經濟夾縫中生長的農村社隊企業。而在一個計劃幾乎包攬一切的時代下,社隊企業在國家工業體系中處于邊緣地位。
“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那時企業**的困擾是拿不到生產的原材料,大多數原材料都是按照計劃配給國營工廠。”黃來興回憶說。而他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購原材料,他為此經常跑上海。在這個當時的計劃經濟重鎮,從國營工廠買回“鐵花花”,其實就是用剩下的邊角料,來作為農機廠生產的原材料。
在上海旅館的大通鋪里,那時經常聚集著和黃來興干著類似工作的采購人員,這也成了一個非正式的信息交換場所。正是在這樣的機緣下,1976年的一天,黃來興經人介紹結識了上海第二汽車底盤廠的一位工程師,并獲知對方想要外包加工一批特殊規格的汽車制動器。黃來興如獲至寶,把這個消息帶回了蕭山。農機廠隨即延聘上海第二汽車底盤廠的工程師做“星期日工程師”,協助進行汽車制動器的研制。
黃來興和同事們從小小的制動泵做起,花了近三年時間,終于在1979年生產出了**臺汽車制動器。也正是在這一年,農機廠將制動器業務分離出來,成立了石巖制動器廠,也就是亞太機電的前身。
但有產品不等于有錢賺。毋庸諱言,彼時的石巖制動器廠還只是一個出身草根、基礎薄弱的社隊企業,企業員工大多是原先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缺乏市場經驗,企業**年就虧損28萬元。
解鈴還須系鈴人。就在企業深陷困局之時,黃來興臨危受命,接任廠長。不了解市場?那就多跑市場。產品找不到銷路?那就去開拓市場。黃來興扭轉困境沒什么訣竅,就是帶頭跑市場,搞調查。然后根據調查得來的市場需求,大刀闊斧地調整產品結構,停止生產滯銷品,重點生產有競爭力的產品,把這些適銷對路的產品推薦給潛在客戶。
為了開拓市場,黃來興經常帶著員工東奔西跑,去各地的汽車展銷會上尋找機會。上世紀80年代初,計劃經濟的堅冰雖已開始消融,但展銷會參會者仍然是按計劃區別對待的,中央直屬國企和地方國企才有資格進場展銷,而鄉鎮企業作為“會外代表”只能在外邊擺攤。
在一場山東膠南舉辦的汽車展銷會上,黃來興與同樣處在創業早期的魯冠球相鄰。正當他們賣力推銷各自產品時,有人從樓上潑下一盆冷水,在冷冽冬日把他們澆了個刺骨寒。當時情景和感受黃來興至今難忘,以至于日后遇見魯冠球時憶及此事,兩人都感慨萬千,感嘆創業維艱。
但一盆冷水,澆不滅黃來興的熱情。那團創業之火已經引燃,火勢漸旺。
一次突破 打破外資ABS一統天下格局
“只有夕陽的企業,沒有夕陽的產業。”黃來興篤信這一點。當記者讓黃來興自己回溯亞太機電何以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社隊企業,成長為國內領先的汽車零部件上市公司時,他謙遜地歸因于一個好時代。要知道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小轎車還是一種具有意識形態爭議的交通工具,要不要發展這一產業,各方一度爭論不休。而如今,你甚至都會覺得這樣的爭論滑稽可笑,小轎車早已駛入千家萬戶。
“1979年全國的汽車產量才50萬輛,現在已經超過2000萬輛,高速增長的汽車產業,為我們提供了不斷擴大的市場空間。”黃來興說。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三大三小”被確立為我國大力發展轎車工業的主要戰略,指定一汽、東風、上汽三大轎車基地和北京吉普、天津夏利、廣州標致為“種子選手”,引進國外合資品牌車型,用市場換技術。出于對國內企業的保護,當時政策力推本土零部件企業對外資品牌的國產化等效替代。
但這殊為不易。就拿汽車制動器來說,當時國內企業相比德日等外資供應商的差距是全方位,在生產工藝、材料、標準化程度上都需要追趕。為了實現對外資品牌制動器的等效替代,黃來興和他的同事花了整整三年時間,終于憑借過硬的產品質量打入一汽大眾、上海大眾等合資品牌的供應鏈體系。
“市場競爭很殘酷,真正的關鍵技術你是買不來的。”黃來興坦言。亞太機電自主研發的ABS(汽車制動防抱死系統)即是典型一例。十多年前汽車ABS還是屬于機電一體化程度較高的高科技產品,發達國家對ABS技術實行高度壟斷與封鎖,既不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又不進行技術轉讓。
1999年亞太機電要上這個項目之前,跑了不少政府部門、科研部門,得到了幾乎相同的回答:市場很大,難度很大,風險不小。黃來興一位曾任博世廣州公司行政總監的朋友獲悉亞太要搞ABS,甚至從香港打來電話,勸黃來興不要搞。
而在黃來興看來,彼時的亞太機電,已有近30年傳統汽車制動系統生產技術積累,有與國內大多數主機廠良好的配套關系,有條件奮力一搏。但事實證明,黃來興友人的擔憂并非多余,在研發ABS的過程中,龐大的資本投入,難解的技術問題、自制檢測及生產設備的艱辛、屢敗屢試的匹配路試、事關行車安全的責任壓力,不斷向黃來興和他的同事襲來。
從1999年立項,到2004年實現量產,亞太機電ABS的產業化之路走了整整五年,企業投資近2億元,真正用于研發的費用真金白銀投入就達到5000多萬元。此前全國投入ABS產業化研發的企業不下百家,而亞太機電成了**家實現液壓ABS系統產業化的國內企業,打破了同類產品由外資品牌一統天下的格局。
一個夢想 劍指國際**汽車配套服務商
對于中國汽車產業,現任雷諾-日產首席執行官卡洛斯·戈恩曾分析認為,中國引狼入室是對的,但是絕對不能到此為止,應該是以狼為師,以狼為師也不應該完,應該是與狼共舞,與狼共舞也沒有結束,最后應該是化虎勝狼。
整車制造的趕超,離不開關鍵零部件的國產化替代。在黃來興看來,亞太機電目前汽車制動器的制造水平,已經不輸于同類外資品牌。公司已涵蓋了100多個系列500多個品種的汽車基礎制動系統、汽車電子輔助制動系統、汽車新材料應用制動部件產品,可以為各類轎車、輕微型汽車、中重型載貨車、大中型客車等車型提供系統化和模塊化配套,產量、規模在國內同行中名列前茅。
在此基礎上,黃來興希望推動公司產品向更智能化、互聯網化、低碳化的方向升級。
比如亞太機電自主研發的ESC(汽車電子操縱穩定系統)已經在進行道路試驗,即將小批量裝車。ESC可以說是智能駕駛、無人駕駛的基礎性技術,在歐美國家已經成為汽車標配,而國內的裝配率也在不斷上升。國內車企主要從博世、天合、德爾福等外資品牌采購,如果順利實現量產,亞太機電同樣有望打破外資品牌壟斷,增添新的利潤增長點。
除了不間斷的技術產品創新,黃來興更力圖通過戰略性投資,來實現對無人駕駛、新能源汽車領域的前瞻性布局。今年以來,亞太機已電相繼投資前向啟創、鈦馬信息這兩家智能駕駛、車聯網領域的新興科技型企業,并共同設立合資公司,作為今后智能駕駛集成產品的研發平臺及一級供應商,合作研發由環境感知的ADAS系統、主動安全控制系統、移動互聯網平臺集成化的產品。
而更具顛覆性的,也許是亞太機電悄然推進的輪轂電機項目。現在路面上在跑的電動汽車,無論是鋰電池、氫燃料電池,還是混合動力,事實上都是靠一個車身里的核心電機驅動的。而輪轂電機的顛覆意義在于,它可以節省大量傳動部件,減輕車身重量,提高整車空間利用率,大大增加電動汽車的續航里程;單個輪胎可以獨立驅動,通過左右輪的不同轉速、車輛甚至可以原地轉,90度水平移動,大大提高駕駛簡易程度。一旦輪轂電機技術實現突破并產業化,它有可能讓現有的電動汽車成為過渡性產品。
“我們已經投資了斯洛文尼亞輪轂電機技術公司Elaphe,雙方約定將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目標是實現輪轂電機的本土化生產。”黃來興告訴記者。Elaphe公司2003年就已開始研究輪轂電機技術,在輪轂電機的電控、生產測試設備及集成運用等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且已具備產業化條件。目前亞太機電和Elaphe在中國合資建廠的計劃已在緊鑼密鼓的推進之中,談及這一項目的未來前景,黃來興無比期待。
從生產機械制動器起步,到如今發力汽車電子產品,布局輪轂電機,亞太機電其實一直都在應時而變。“但專注圍繞汽車產業鏈服務配套的戰略不會變。”黃來興說。
這是屬于一位70歲企業家的,另一種汽車夢。